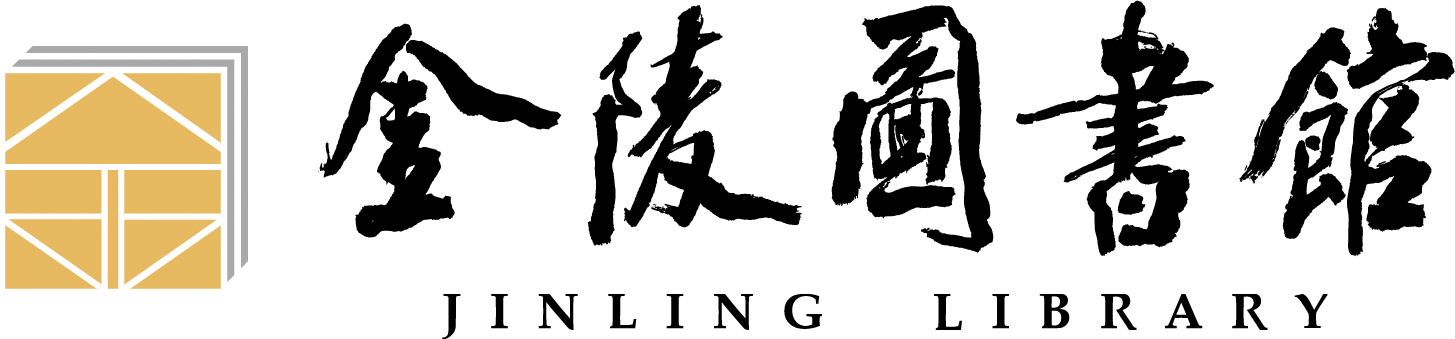![期刊架位号[2390] 期刊架位号[2390]](./W020250329377303867745.png)
“第一件事”的说法来自朱熹的一句话,即“亲亲、仁民、爱物,三者是为仁之事。亲亲是第一件事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二十)。“亲亲”一说来自孟子的“亲亲而仁民,仁民而爱物”(《孟子·尽心章句上》)。“亲亲”指人与人和谐(仁民)、人与自然和谐(爱物)。人与自然的关系、人与人的关系,是中国式现代化基本范式要回答的元初问题,因此是“第一件事”。
2024年12月10日,北京大学“中华文明与世界未来”研创会专家策划会在北大经典与文明研究中心举办。据北大经典与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戴熙宁介绍,“中华文明与世界未来”研创会这个学术平台背后的问题意识,在于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,即“整体性不够、系统性不强、碎片化倾向严重”。因为百年以前,新文化运动引进了科学和民主之后,引进了西方的分科学术范式,造成了目前这个局面。当前,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,即构建中国自主的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,就要回归我们自身文明的基本范式。
一、中华文明和世界未来正处于奇点时刻,需要一个引领性的范式指出方向,这个范式是亲,即“‘亲亲’是第一件事”
我觉得探讨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特别有意义。首先,时间选得特别好,我希望历史能够记住,这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未来的一个奇点时刻、转向时刻。上一个这样的时刻出现在伏尔泰、卢梭那个时代,通过理性彻底扭转了人类的方向。今天,从启蒙运动到现在的工业社会,面临向信息社会的一个转折点。这个转折点需要新的范式,我特别赞成讨论范式问题。
我认为在这个奇点时刻,要提出一个词囊括这一切。2017年11月22日,我在新加坡旧国会大厦做过一个演讲。我认为,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世界的未来,不在于谁统一世界,而是形成一个和西方式现代化的核心理念“理性”对应的范式概念。世俗的东西发生了变化以后,这个范式不变,但在全世界能够继续引导未来。
上一次奇点时刻的范式确定任务完成了,是伏尔泰他们主导的,他提出一个“理性”就解决问题了,剩下的全都是鸡毛蒜皮。那么,按照“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的顺序,我们先讨论“一”。这个“一”是什么?我认为,如果从白到黑再到白这样一个正反合逻辑来说,我们要提出和中间这一段(理性)相反的一个概念。那么,与理性相反的概念是什么呢?是“亲”这个范式。
“亲”是什么?笛卡尔提出理性,朱熹也提出理性,但我认为二者是反义词。反在什么地方?笛卡尔所提理性是“心物二元”的理性,朱熹所提的理性是“心物一元”(中国称“天人合一”)的理性。理性的反义词不是非理性,而是朱熹所说的“亲”。朱熹认为,“亲亲是第一件事”。“一”是理,这个“理”解为“亲”, “亲”就类似“生生之德”, “生”解释为“生生”,“亲”也解释为“亲亲”。这两个“亲”,第一个“亲”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,人与自然的关系要“亲”(和谐);第二个“亲”是人与人的关系要“亲”(和谐)。它和理性“反”在哪儿?笛卡尔的理性,是两不亲:第一是人和自然不亲,第二是人和人不亲,这是整个工业文明的核心范式。所以,我认为,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,那么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,这个亲民不仅是亲民,而是“亲亲”,既涉及自然,也涉及人,把自然和人的逻辑统一在一起,也就是“民胞物与”。我把这个范式概念概括为“一体之仁”,既能管自然科学的事情,也能管社会科学的事情,一以贯之。这不是反转,而是扬弃,即接受工业文明、接受理性,但是在更高的层面上,把朱熹所说的理性的“亲亲”与中国文化的“生生之德”贯穿起来。
二、亲亲的第一个亲,是天理学,即自然科学的古典学,可以引领未来高科技发展方向
亲这个“一”,生成亲亲这个“二”的第一个方面,也是我的第一个层面的结论,讲人和自然的基本范式,我们称为“天理学”。
宋代儒学将儒学天理学发扬光大。孔子晚期的易学转向,以及子思子之学,也就是中庸、大学之道,肯定天命之谓性、率性之谓道。到了宋朝,把人与自然的关系、人与人的关系融为一体,使儒学思想成为一种兼及自然与人文的普世价值,不仅是解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,还要解释人和自然的关系。
李约瑟认为中国有技术没科学。我认为中国有科学,称为天理学。现在我们要接续到一切有活的特征的事物里。用李曙华老师的说法,活的特征就是生成,要接续到复杂性系统的涌现生成之理上。第一是信息科技,也就是人工智能,第二是生命科技,都跟“气”有关。我认为今天的范式扩展一步就是古典学。古典学就是判断什么是科学、什么不是科学的基准。我们称基准而不说“真理标准”,因为真理应该用实践做标准。现有全球大学中的古典学基准是古希腊之学。中国有没有古典学?我认为有,就是宋代以后,四书五经实际建立了一个东方基准,只不过其中的自然科学逻辑没有展开,但这个逻辑是潜在存在的。
我认为有三条基准,判断什么样的自然科学是科学的。第一是心物关系,第二是时空关系,第三是体用关系。中国的基准是三亲,一是心物相亲(天人合一),二是时空相亲(宇宙一体),三是体用相亲(知行合一)。西方的基准是三不亲,一是心物不亲,二是时空不亲,三是体用不亲。在西方科学观看来,要想成为科学的,一定要三不亲,而量子力学出现后,这种观念开始受到挑战,开始转向。
(一)第一个基准是心物亲不亲(合一还是二元)
西方认为只有心物二元的才是科学,心物一元不是科学,甚至是伪科学。我认为现代科学正在向着心物一元的方向发展,最典型的如量子力学,将张载所说的天地之心以弦的存在加以肯定。天地有没有心,在量子力学里得到了一个主流化的验证。虽然朱熹所说的天地之心是“无思量底”,也就是说不依托于大脑,但是具有与“思量”(如“灵明”)相同的不确定的根本特征。比如,在人工智能领域,李德毅院士根据认知物理学提出的不确定性人工智能,把机器认知视为天地之心,回应了李曙华老师的疑问,就是中国能不能有原创性的人工智能的思路,把科技派和伦理派融为一体。我认为底层逻辑是心物一元,也就是天人合一。西方的人工智能误入歧途,主要原因是把信息当作物质现象来解,没把天地之心给解透,不能适应不确定性。对于这一点,我们有很多院士已有共识了。这个共识就是提出了“数据场”的概念,成为中国人工智能及下一代高性能计算的主导思想。
(二)第二个基准是时空亲不亲(合一还是二元)
按照一体之仁,时空是一回事,宇和宙不分开来说,但是西方人一直是把时间和空间分开来说的。按西方科学标准,时间和空间不是一回事,时间和空间要是一回事,就是伪科学。可以以这个来验证李曙华老师所说的象数。象数的本质是什么?如果只有数,在图论里,就只有计数功能、节点功能。网络是节点加上边,实际上融入了时空概念,其本质是把时间融入空间,也就是拿一幅图画来当作计算的基本单位。
在中国的算经(如《周髀算经》)里体现的中国数学体系的要领是“化”,也就是在圆和方之间化来化去,化圆为方、化方为圆,表面上是在解方程,实际是用方程形式化“易”(becoming,生成变易)这种“化”。圆和方的“象”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生成,这才是中国数学精神的实质,其实也是现代数学一个前沿的发展方向。它可以成为量子计算的数学基础,因为量子比特是叠加态,既不是0(阴),也不是1(阳),而是三(代指转化)这种叠加态。
未来的数学和中国一体之仁的时空标准有密切关系。
(三)第三个基准是体用亲不亲(合一还是二元)
中国科学的基准是体用一元。西方人认为普遍的东西一定适用于一切地方,如果因地制宜、因人而异、因时而异,就不科学,比如中医。中国认为只有体用一元才是科学的,科学原理要和具体时间、具体地点、具体场景结合。
在人工智能领域,就体现为场景驱动。不仅要讲人工智能的通用(如通用人工智能),在通用之外,还要讲场景,要依靠本地上下文语料库,以及端的计算,与通用解释结合,基于语用,得出每个人所需要的不同答案,实现具身智能。
我认为这三条标准意味着关于什么是科学、什么不是科学的标准的根本性改变。从伏尔泰开始立的规矩,现在出现了转向。这种转向不是否定西方科学,而是指西方科学要朝活的、有生命的事物这个方向去转向,这个就是天理学。
三、亲亲的第二个亲,是亲民学,即社会科学的古典学,可以引领未来信息社会发展方向
亲这个“一”,生成亲亲这个“二”的第二个方面,也是我的第二个层面的结论,即人和人的基本范式就是把亲这个范式用到社会理论,我称之为“亲民学”。
亲民是《大学》提出的儒学核心思想之一。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,这个纲领进一步简化,就只剩亲民。王阳明认为,“明明德者,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。亲民者,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。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,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”。这就把亲民当作明德的所以然。亲民联用,与天理相对,更多的是指人与人的关系。亲民与天理不是两个东西,而是一个东西,都是亲亲,可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理论判断是否正确的总的指向。
(一)第一条社会基准:心物亲还是不亲——决定战争与和平
第一条基准是从心物亲还是不亲(合一还是二元)来讲的。第一条基准,讲的是心物是一元还是二元。心物二元得出的结论是从卢梭开始所讲的委托代理,一切都要别人代表,一切都不靠自己,除了吃饭、上厕所外,其他都不能亲自。一体之仁也就是心物一元、天人合一强调的“亲”,是要亲自创造世界、享受世界,用数字经济的术语表达,就是access(亲自,参与)。翻译过来,就是“要创造人类的幸福,全靠我们自己”。再翻译回去,用孔子的话说就是“君子笃于亲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。
委托代理过头了,人本能地要反抗。要建立一个什么世界呢?最近我们提出“可信”的数据空间。这个“可信”指的是信任,不是信用。亲和互联网发动机的原理“最短路径优先(OSPF)”在数学上是等价关系。我们只有由近及远,才能使这个世界变得实在。一不亲,就生分了,就容易异化。
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理性,用“亲”(复归)替代“不亲”(异化)。而西方式现代化的“不亲”(笛卡尔理性),虽有一定进步意义,但一旦走极端,就表现为战争、冲突等,这都是不亲。社会理论是否科学,要看其最终引向战争还是和平。因此,亲不亲的问题,是一个《战争与和平》的故事。以不亲为社会理论是否正确的基准,才会引出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实属必然的结论。中国不是这样,对战争本质的理解是和平,即止戈为武,是因为骨子里以亲为文化基因。中国不是不能打仗,而是不以“不亲”为主动追求而打仗。工业化这几百年来,这个道理就没有正过来,现在要正过来。
(二)第二条社会基准,时空亲还是不亲,决定合情与合理
第二条基准是从时空角度讲是亲还是不亲(合一还是二元)。西方文化中,空间对应理智,时间对应情感。萨尔瓦多·达利(Salvador Dalí)在《流淌的钟表》中,用时间隐喻情感,显示出情感状态会显著影响人们对时间的感知。西方社会观念中,讲理的世界是科学的,不讲理的世界是不科学的。但我们要讲合情合理,西方是合理不合情。这里所说的不合情,不是说情不能存在,情可以存在,但只能存在于生活世界,不能存在于生产世界。例如,熟人关系只能在私下场合讲,商务方面还是要讲公共关系。
中国古代讲礼乐文化,礼讲合理,乐讲合情,在讲理之外,还要讲情。《乐记》强调礼乐虽通达天地,但也通于人情,“礼乐之说,管乎人情矣”, “夫乐者乐也,人情之所不能免也”。GDP是合理的,但离开了幸福快乐,就会失去意义。《乐记》还强调了乐是心物感通的,“乐者,音之所由生也,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”,这也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意指结构把快乐物化的取向。
情,象征着时间渗透到人的社会关系,如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,也就是社会空间里也有情的存在,改变了社会历史的松紧尺度。中国古代合情合理的观念,代入数字时代社交商务中人与人的关系模式,就成了“陌生的熟人”的关系,既要讲适用生人关系(公共关系)的理,也要讲适用熟人关系的情。
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中强调东方基准,本质上要求的是生产世界复归生活世界,让合理复归合情。
(三)第二条社会基准,体用亲还是不亲,决定变通还是不变通
第三条基准是从体用角度讲亲还是不亲(合一还是二元)。
程颐在其主要著作《伊川易传》中说:“至微者理也,至著者象也;体用一源,显微无间”。王阳明也主张体用一源,在《传习录》中说:“中只有天理,只是易。随时变易,如何执得?须是因时制宜。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。如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罅漏。立定个格式。此正是执一。”
体用一元就是要把某某特色和某某道路结合起来,任何普遍的东西都要做本地化的改进。我们称之为语境化,也就是说不要孤立地讨论抽象文本(如某种教条),要把文本放在其上下文语境里来具体理解,儒学称此为实事求是。
西方的古典学逻辑却不是这样,总是以为普遍的东西适用于一切地方。如果因地因人因时而异,一定是不科学的。而一旦认为体用二元对社会逻辑来说才讲得通,会片面强调抽象、普遍、普世,最大问题就是不实事求是。
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关系,也要讲具身智能。如果只讲通用人工智能,不讲端的智能,千人一面,众口一词,这个世界就会失去丰富多彩性,就不会变,也行不通了。
我认为,有了这三条原则,就可以用“亲亲”来纠正“不亲”造成的种种问题。我相信,这个儒学不仅是我们的,欧洲也可以看到,比如绿色和红色结合起来。红色是人与人之间的亲,绿色是人与自然的亲,他们早晚会知道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。未来应该是东西方融合的,这个世界当不亲过了头以后,就得拿亲来进行中和。
北京大学“中华文明与世界未来”研创会专家策划会的主持人戴熙宁对于“奇点”和“亲”提出了他的观点。一是关于“奇点”,提到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。“又一次的思想解放”,是40年的历史概念;“又一次新文化运动”,是100年的历史概念。但是当今面临的范式转型,确实是1000年的历史概念。二是关于“亲”。《周易·系辞》中说“乾以易知,坤以简能;易则易知,简则易从;易知则有亲,易从则有功;有亲则可久,有功则可大;可久则贤人之德,可大则贤人之业。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。天下之理得,而成位乎其中矣。”。文明靠人的凝聚,要“亲”;人的凝聚靠统一思想,要“易知”。统一思想的知识体系和学理体系,在中国就是“易”,即“生生之谓易”。网络时代,万物高效率互联,但价值和效率却不统一,也是当今人工智能最大的问题,即人机价值不匹配。这个问题在西方文明体系里没办法解决,因为西方的科学与宗教是分开的。人工智能时代,自然要回到中华文明的范式。
(《互联网周刊》2025年1期 [2390])